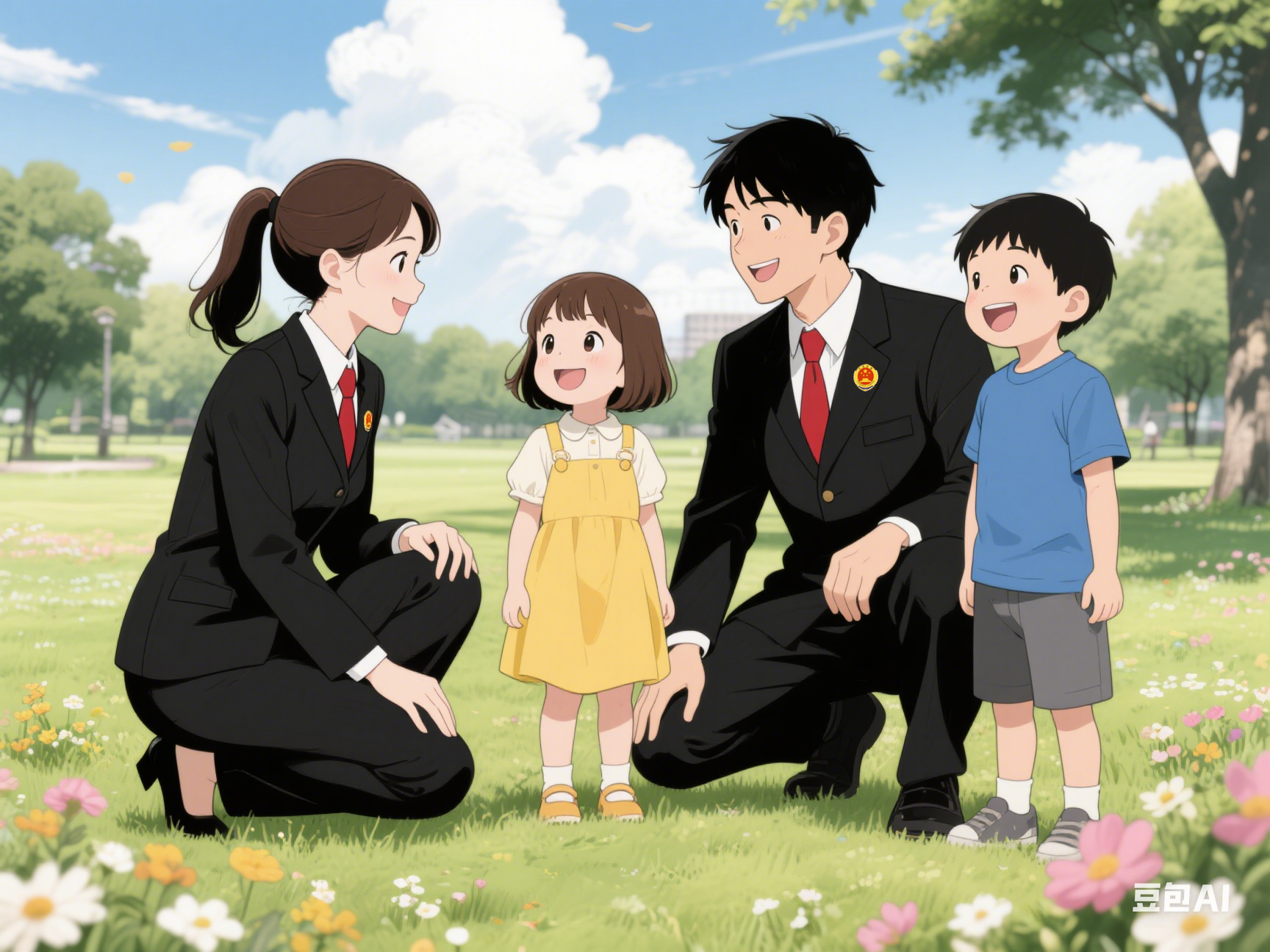十八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海安,就是为了守护在母亲身边,方便照顾她。可回来那年夏天,母亲吃饭吞咽困难,在乡镇医院做了胃镜检查,检查报告没有“癌”这个字。我与大哥又把检查报告和母亲带到县医院,请相关专家诊断。我们把母亲安排坐在医院走廊里,大哥到门诊排队挂号,再到专家门诊室排队。我一直陪着母亲,心里默默祈祷∶可别是什么不好的东西(癌变之类的)。

“老五,来一下。”大哥在专家门诊室喊我。我进去了,那位外号“××医院一把刀”的专家稍沉思了一下对我们兄弟俩说∶“你母亲食道癌晚期,位置…”我没等“一把刀”说完就溜到卫生间了,我面对墙壁,默默地叹气流泪。
本想转业回来让母亲过一个幸福的晚年,怎么就这么巧,偏偏这个时候癌降临到母亲的体内。
我用衣角擦干了眼泪,走出卫生间,不敢直视母亲,又怕母亲从我眼里看出什么,又到专家门诊室。大哥和“一把刀”安慰了我一下,商量治疗方案,第一种是手术,但有风险,癌变位置对这么大年纪的人来说,不适宜;另一种就是化疗。根据“一把刀”的建议,就确定化疗。可怎么对母亲说呢?
“一把刀”让喊母亲到门诊室,我又溜出去了,站在窗户前,忍不住流泪,不知生我养我的母亲还能活多久,化疗的副作用,母亲能不能挺得住。
“老五!”大哥叫我了,“我们回去准备生活日用品,明天来办住院手续”我搀扶着母亲慢慢地向医院大门走去。在医院大门口叫了辆人力三轮车,我让大哥和母亲坐三轮车去车站,我紧跟在后面,看着三轮车尽量走平坦点的路面。
从汽车站坐车到离家四里多的地方,我骑自行车驮着母亲,尽量慢慢地骑行,甚怕因路不平颠簸。到了家,其他哥嫂和左邻右舍,都相继来问长问短。我一概不回,默默的陪着母亲,准备住院的生活用品,熬粥,把粥表层稀一点的,专门盛碗里凉一会儿,留给母亲喝。

第二天,还是大哥与我陪着母亲到县城的医院,办好了住院手续,我陪母亲做住院前的一系列检查,大哥去病房确定床位。跑了半天,有的检查还没做完(以后的几个疗程,没必须检查的项目就不做了),到了病房,让母亲尽量半躺着,等着挂水化疗。由于刚安排工作,我不能全天陪着母亲,只能下班后陪着母亲,白天由哥姐和嫂子们陪。晩上,我给母亲洗脸,擦身,洗脚,尽量少让母亲吃力,削苹果,用勺子刮苹果泥给母亲吃,每天轮换着口味不同的牛奶和其他品种不一样的传统的汤水,让母亲感觉到我尽可能给她好的侍候。那时没听说过营养液,也没果汁机,每隔两三天到做豆腐的邻居家舀一大碗豆浆,白糖、老红糖轮换放,给母亲喝。
三个疗程下来,母亲明显匮乏了,头发变稀了,尤其是没力。在家里的时候,我就借“一把刀”的话鼓励母亲∶不怕多吃(事实上只能吃流质),营养跟上,疗效更好。晚上下班从县城买母亲合适的流质饮品,因为那时没冰箱,只能少买,常买。晚上到家,像照应自己孩子一样,看母亲躺下了,我才能睡着。
为了陪母亲也顾不上老婆孩子了,受点委屈也很正常,这个时候也能接受任何委屈。
记得母亲在最后一个疗程结束出院时,要到我租住的人家看看我临时住得怎么样,我们满足母亲这个愿望。到房东家看了看,母亲还对房东说∶“麻烦你帮助照应我伢儿啊!”这话听得让我心酸,母亲似乎预料自己活不多长时间了。当时自己预订的房子还在基建过程中,离租住的地方也不远,但不便看。这一次母亲回去之后,就再也没能去哪儿。

母亲临终前的早上,我抱扶着她坐起来,给母亲弄了小半碗蛋花,母亲吃力地喝了一口,我抱扶着母亲走出房间。我说∶“妈,我去××了(县城的名字,言下之意我去上班了)。”母亲眯着眼纠着脸吃力地说∶“慢一点啊!(言下之意∶注意安全)”谁知中午大哥电话说母亲可能不行了,我赶紧请假,从丈人家叫上老婆孩子一起回去。母亲静静地躺着,还有模糊意识,她还有一个儿子,我四哥在赶回的路上,我四哥一到家,喊了两声“妈!”,母亲微弱地睁开眼,似乎看到儿孙都在身边,永远地闭上了眼晴。
为了多陪母亲,母亲遗体在家里停放了按照农村风俗的最长时间,每当隔着冰柜看着母亲,觉得她还保持着生命的气息,睡得很安详。
母亲不在了,才理解∶母亲在,自己永远是个孩子。如今自己也是“房东”了,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仅以此文,表示对母亲的怀念。